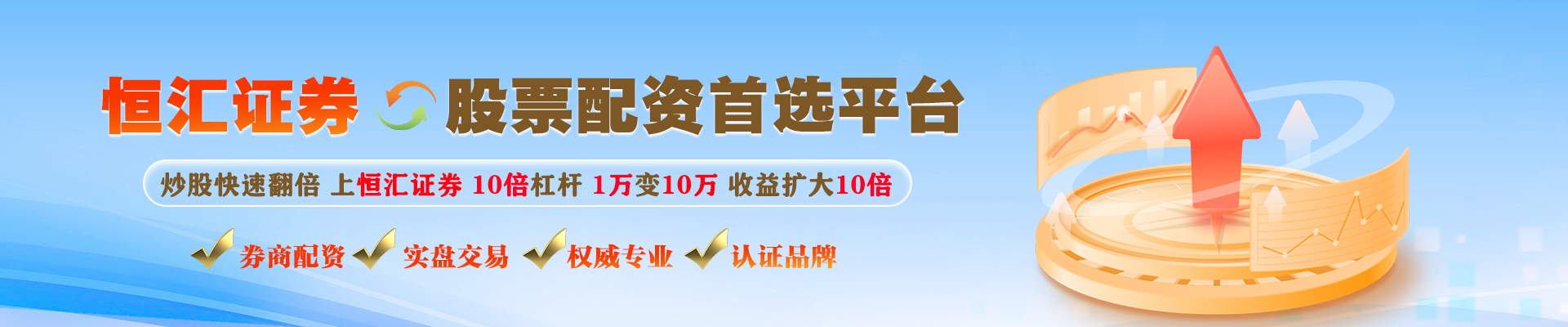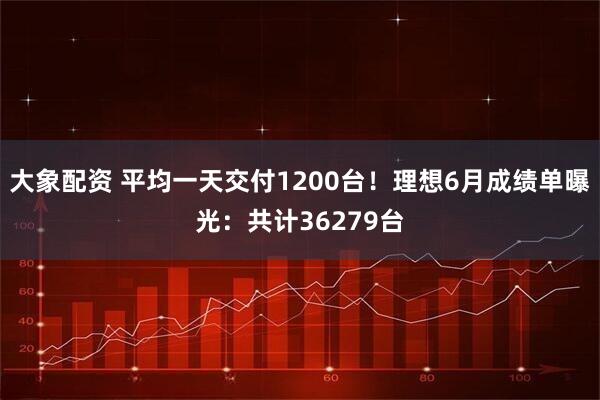融318配资 龙首山下(第三十六期)手写的温度,未凉

那 年 那 月
手写的温度,未凉
张萧汉
前几日回母亲家收拾旧物,在木箱底翻出一枚泛黄的牛皮纸信封。边角发毛,墨色晕染,邮票只剩淡影,可指尖抚过那规整庄重的字迹时,忽然触到一丝温热——那是三四十年前手写书信独有的温度,穿越岁月风尘,竟从未真正凉去。信封落款是“哈尔滨”,收信人是父亲,寄信人是大姑家的大表哥,这枚被时光啃啮过的信封,藏着全家对冰城亲人沉甸甸的念想。
指尖抚过那行字,几十年的光阴忽然倒流。那时,手机与网络尚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寻常人家的牵挂,全靠一枚邮票承载,翻山越岭,辗转抵达亲人的掌心。父亲有一兄二姐,大姑是长女,年轻时为了一段姻缘远嫁哈尔滨。二姑和大伯都在开原。自此,那座遥远的冰城,便成了全家心头一份沉甸甸的、北方味的念想。
念小学时,给大姑家写信的“重任”便落在我肩上。即使过去了几十年,我还清晰地记得大姑家的通信的地址——哈尔滨市太平区三棵树大街251号,彼时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如今高楼林立异常繁华,251号也许就是档案馆里的印记和我脑海里的思绪。
展开剩余91%与我通信的对象,主要是大姑家的大哥,他长我十几岁。我们的信里,从无大事,尽是些琐碎如尘、却又闪着微光的日常。我写院中樱桃又红了,一颗颗亮晶晶的,等大姑回来尝;写我得了一朵小红花,老师夸我字有进步;写父亲总念叨,说大姑爱吃的粘豆包,母亲今年蒸得格外多。大哥的回信,也总是絮絮叨叨的:哈尔滨的雪真大,屋檐垂下的冰溜子像透明的钟乳石;姑父厂里发了一袋大白兔奶糖,他偷偷为我留了几颗;大姑腌的酸菜出缸了,炖粉条时满屋的酸香,让她想起老家的灶台。
信,写得慢,寄得也慢。从辽北小城开原,到冰封的哈尔滨,一封信要走七八天甚至更久。等待回信的日子,被拉得细长,成了一种磨人的甜蜜。每天放学,我总绕道村口的邮政代办点,踮起脚扒着木柜台,眼巴巴地问:“有哈尔滨的信吗?”若得到一声肯定的、拖长了调的“有——”,接过那封带着远方邮戳与陌生气息的信,心便倏地胀满了。一路攥着跑回家,连书包都来不及卸,就急于用指甲小心地启封,展开信纸,那熟悉的字迹便带着北方的寒气和亲人的暖意,扑面而来。
那时节,路远,囊也涩。大姑一家回趟老家,需坐近十个小时的火车,再倒颠簸的汽车,历尽风尘,往往数年方能一聚。相聚时的喧腾欢欣,别离时的默默拭泪,最后都沉淀为一笔一画,安放在信笺里。记得有一年春节,他们终于回来了。小院被欢声笑语塞得满满当当,厨房里雾气蒸腾,猪肉炖粉条的浓香、粘豆包的甜糯气交织弥漫。姑父与父亲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就着一碟炸花生米,抿着辛辣的散白酒,话头起起落落,都是这些年积下的光阴。大哥悄悄拉我出去,在村口小卖部买了几颗水果糖,糖在嘴里慢慢融化,那丝丝缕缕的甜,仿佛能渗到记忆最深处。
后来,家里装了固定电话,遥远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可闻,那份等待的仪式感却也淡了。及至手机普及,联络瞬间可达,只是信纸上那些流淌的、温热的絮语,化作了电话里三言两语的问候,变成了微信屏幕上简短的字句与飘忽的表情。再后来,像秋风扫过枝头,大姑和姑父相继凋零,父亲也故去了。那座冰城,在心理的地图上骤然黯淡下去。与哈尔滨的亲人,只剩年节时微信列表里一句群发的祝福,一个习惯性的点赞,已是十数年未曾谋面。
我捏着这枚空荡荡的老信封,暗自神伤。内里的信纸早已不知散落何方,可那些藏在横竖撇捺里的牵挂,那些在等待中发酵的期盼,却比任何实物都更牢固地存留着。这薄薄一纸,曾是亲情的血脉,它笨拙地、缓慢地搏动着,输送着思念的温度,跨越地理的严寒,将两颗心妥帖地连在一起。
如今,万里之遥已成咫尺,音容笑貌即时可见。可不知为何,情感的浓度仿佛被这便捷悄然稀释了。我们不再肯耗费半日,铺纸磨墨,将心事细细倾泻;不再有机会体验那种日复一日翘首以盼,最终收获时近乎颤栗的喜悦。一句“新年快乐”群发四方,一个“笑脸”表情包涵盖所有,千言万语,似乎都嫌啰嗦。
风从窗隙潜入,拂过掌心脆薄的纸张,窸窣作响,如同时光的耳语。我忽然想起,大哥的孙子,如今也该有我当年伏案写信的年纪了。他可知晓,在某个没有Wi-Fi信号的年代,他的祖父与一个远在辽北的堂亲,曾依靠这种古老的方式,将千里之遥走成一条温暖的虚线?
我把信封放进洁净的盒子,它不是空壳,是手写温度的见证者。此刻忽然笃定,要拾起久未动用的笔,给哈尔滨的大哥写封信:说说老家樱桃树又红了,母亲蒸的粘豆包还留着他爱吃的甜糯,问问哈尔滨的冬天,是否仍有半尺长的冰溜子。就像从前那样,让墨迹慢慢流淌,让牵挂细细铺陈,让这份手写的温度,在仓促的当下,重新温暖彼此的岁月。
(张萧汉,在职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偏爱在书页间拾撷诗意,于旅途里收藏风景,愿将心底温热、人间清欢,都化作温润笔墨,静静诉说岁月里的温柔与美好。)
一碗大酱
柴宝侠
如果爱有颜色,它一定是缤纷的。或许是黄色的,就像一碗大酱所承载的父爱。
记得那年端午节,我们姊妹5个,相约回老家看望父母。
每次回家,我就一头扎进父母的小菜园,采摘绿色蔬菜。
我家院子很大,前后有一亩多地。父母很勤劳,他们把自家房前屋后的菜园打理的井井有条,后院有果树、蔬菜。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大葱、圆白菜等。前院是各种妖娆的绿色小菜,香菜、生菜、菠菜、小水萝卜等各种蘸酱菜,都是我的最爱。
那些浸透着父母心血和汗水的绿色蔬菜,顶花带露,水灵灵像新生婴儿一样,带着泥土的芬芳,伸展着碧绿的腰肢,透着一股清新的味道,家的味道,爱的味道。
每年父母都要多种一些蔬菜,等我们像燕子一样飞回去时,大包小包地给每个孩子往城里拿菜。
父母常常说:“家里的菜吃着放心,不用花钱,过日子能省就省着点。”
我拿个小筐,像蜜蜂采蜜一样,尽情地在菜园采摘喜爱的果蔬,迫不及待地想品尝绿色蔬菜的美味。
“妈,还有大酱吗?”
“哎!那天我没在家,酱缸蒙子刮掉了,掉进去一只家雀,大酱不能吃了。”
我一听,明亮的双眼瞬间灰暗下来。碧绿的葱叶,水汪汪的小菜,没有大酱,就像吃饺子没有醋一样,让人扫兴。
父亲看到我失望的表情,没说话,悄悄地走了。
我和姐妹们摘菜,剁馅,包饺子。姐弟几个不常见面,一见面像家雀一样叽叽喳喳,边干活边唠家常。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两盖帘元宝饺子包好了。母亲说,让你爸烧水煮饺子。
“爸!爸!烧水煮饺子…咦,人哪去了?”东西屋都找不到父亲的影子。大家以为父亲去屯里溜达了。母亲唠叨着说:“这人真是,孩子们都回来他还出去。”
大家正七嘴八舌像家雀一样叽叽喳喳说笑着……
我猛一抬头,目光望向窗外。
只见苍然白发的老父亲,佝偻着背,双手颤颤巍巍捧着一碗大酱,一步一挪,艰难地从大门外挪进院子。瞬间泪雾弥漫,父亲,你怎么就老了呢?端一碗大酱都那么困难吗?
我一直以为父亲不会老。他总是腰板挺得溜直,两条大长腿走路大步流星,说话大嗓门,性格大大咧咧,从来不跟人计较生活琐事,整天乐乐呵呵笑对生活。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也以乐观的态度过一天乐呵一天。我以为这样乐观的人不会老。父亲唯一的心病就是手抖。多年来,子女们寻医问药,也没能治好父亲的这个毛病,在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件憾事。
我趿拉着鞋,飞奔着冲向长长的院子,从父亲颤抖的手里接过大酱碗。酱香扑面而来,家的味道瞬间濡湿我的双眸。问父亲从哪里端来的大酱。他说,是你大姨家的大酱,也非常好吃。
双手捧着那碗焦黄、喷香的大酱,我忍不住泪落。
大姨家在村子的最南端,我家在村子的正中间位置。两家相距大约2000米左右的样子。从大姨家到我家是个斜坡,步步上岗,父亲是怎样用那一双颤抖的手,步履蹒跚地将那碗大酱小心翼翼地捧回家的呢?
他每挪动一步,对孩子的爱就更深一层。他走过的坡路,留下一行行父爱的足迹。
望着这碗盛满父爱的大酱,我不敢动筷,不敢触碰这份沉甸甸的爱。
曾经以为父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对我们几个子女不太上心,从小到大都是母亲在辛勤地操劳照顾着我们。此刻,父爱潮水般在我心中奔涌。
我不知道这碗酱真实的分量。但,端在我的手里,却无比沉重……
世界上最难称量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就像这碗芳香四溢的大酱。
(柴宝侠,生活的歌者。愿以文学为光,沐光而行,采摘生活的蜜糖。)
奶奶家的春节
李美希
奶奶家的春节一向是很热闹的。
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每年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不只是因为过年可以做很多平时不能做的事,还因为过年意味着可以回奶奶家,对于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我们来说,农村大山里的奶奶家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乐园。那时,在外工作生活的父辈们都拖家带口地回到故乡过节,一向平静的村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且不论大人们怎么样,于我们孩子而言,那段时间可能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有很多小伙伴,有平日里很少见到的各种小动物,没事的时候,只需走几步或喊一声,就能找到十来个二十来个小伙伴,有兄弟姐妹,也有辈分高但年纪小的姑姑,一群人像关了许久的鸟儿一样,在不大的小村庄里尽情撒欢。
身后偶尔也会跟了一条不知谁家的小狗,随着我们满村跑,小孩子年纪小,精力旺盛,玩着玩着经常会忘了时间,总是要等到日落西山,夕阳洒在天空上,家家都冒起了炊烟,做好饭的大人们站在门口喊几声才肯恋恋不舍的告别伙伴回到家里。
很快,天就彻底黑了下来,晚间的活动比起白日就少了很多,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早早就铺好了床钻到暖和的被窝里看电视或聊天,家里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或在屋子里玩笑打闹,或在院子里放一放小的烟花,偶尔玩累了,抬起头,大山里的空气明显比城市里好的多,无数的星子挤挤攘攘的洒在黑色的幕布上,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也一时让人分不清画家到底是把金色的颜料洒在了夜幕上还是在金色的空隙填涂了黑色的颜料。
夜渐深,看电视的关了电视,打闹的钻回被窝,很快村子里便陷入了沉寂,只有家里的小羊小牛在睡梦中偶尔发出几声低语,我想,它们可能也在做一个甜甜的美梦吧……
当然,最热闹的要数年夜饭了,奶奶家的年夜饭可不只一顿,今天这家办,明天那家办,总要吃个几天的。那时,几乎全村的人都聚在一家,大人们很早便屋内屋外的忙着做菜上菜摆盘,照例是床上一桌地上一桌的,床上是孩子,地上是大人。我们开心,村庄里各家养的小猫小狗也开心,摇着尾巴穿梭在桌子之间,等着谁偶尔往下扔的一些吃的,孩子们是很乐意惯着它们的,肉、虾、鱼……自己吃一口也要喂它们一口,据说,过完年我们都陆续回到城市里回归自己的生活后,这些小猫小狗们总要挑食一段时间呢!
过不了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吃完了,而大人自然要喝酒聊天好久,小孩子坐不住,吃完不久便无聊了,于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或爬山或滑冰或跑到谁家里去和小羊小牛们玩,家长们也不担心我们跑丢了—村子就那么大,总能找到家的。玩累了,就随便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来,聊聊现在;聊聊过去;聊聊梦想,一起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现在想来,儿时那段时光是美好的,热闹的。也很庆幸我能拥有那么一段快乐的回忆,让我每当想起童年,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是那时的热闹景象,虽说现在老家的年味越来越淡,但那段时光会如同儿时看到过的满天星子般,璀璨的闪烁在回忆的夜空中;也将成为一个珍藏的宝盒,安置在自己记忆的阁楼里。
(李美希,00后大学生,爱生活、爱文字,收录生活中的感动,记述生活中的精彩。)
街 巷 烟 火
岁始三味
包新宇
新年的头几日,天气总是好的。这时候,人坐在书桌前,心里便无端地生出些安详的念头来。
我倒没有什么宏大的新年誓愿。年纪渐长,便觉得把日子过出些滋味,比达成什么目标更要紧。像汪曾祺先生说的,“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这新的一年,我想做的,也无非是几件能让心里“小暖”起来的小事。
头一件,是想学点中国的文人写意。工具是现成的,去年友人赠了一刀生宣,几支羊毫,一直收在柜子里。颜料也不必复杂,赭石、花青、藤黄、胭脂,有了这四样,大约山石草木的精神便能描出个大概了。我并不想成什么画家,只是觉得,看了一年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那些颜色与形态在心头印下了,总想找个法子“留”下来。文字固然能写其神,但终不如笔墨能直接摹其形色之万一。也不求形似,但求一点意趣。譬如看见墙角将枯未枯的芭蕉,那一片焦黄中透出的筋脉,便想用淡赭混着墨,在纸上扫出那么一片风雨的痕迹来。画得好坏是其次,这观察与涂抹的过程,想来便是有味的。这大约也算是一种“格物”吧,用笔尖去体贴万物的姿态。
第二件,是关于吃的。我忽然想自己试试发豆芽。从前总在集市上买,一丛丛白生生、水灵灵的,看着可喜。今年想从一粒绿豆做起。找一个阔口的陶盆,铺上洗净的细沙,将挑好的豆子匀匀撒上,每日用清水淋过,再用深色的布蒙了,避光。然后便是等待那点嫩黄的小芽,顶开豆壳,伸出白嫩的茎,一日日变得肥壮。等发好了,也不必复杂烹调,用滚水一焯,淋几滴麻油,撒一撮盐,便是极清鲜的小菜。自己劳动得来的这一点“青”意,拌在粥饭里,味道想必是不同的。
还有一桩,是想重新亲近我的书架。不是泛泛地读,是想挑几部一直总没勇气打开的大书,慢慢地“啃”。比如《水经注》。从前只当它是地理书,翻过两页,觉得枯燥。后来听人说,这书的好处,在文字简净,有山川的魂魄。便想挑一个安静的下午,泡一壶浓茶,跟着郦道元的笔迹,神游那些古老的江河。他写三峡,“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写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这些句子,光是低声念一念,便觉唇齿间有清冽的水汽与浩荡的风。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便不是求知,而是游历了。一年若能这般“游历”一两部书,精神便算有了好的滋养与栖居。
新的一年,不是一张需要费力填满的考卷,而是一本素白的册页,等着我用这些琐细的笔墨,一天天地,从容地,填写下去。
(包新宇,90后,一位坚定的生活家,深信每一天都是礼物,用文字拥抱现实中的每一缕阳光与风雨。)
山居冬亦暖
朱志勤
时间过得真快,退休后回到这座山村老宅,一晃已经五年了。这些年,春、夏、秋三季,真是我最快活的日子。
每年一开春,山就醒了。桃花、杏花、梨花、樱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热热闹闹地开满坡。到了六月,洋槐花一开,更是不得了,满树雪白,香得人走在路上都忍不住深深吸几口气,那甜丝丝的味道,能一直透到心里去。
夏天是我的小院最丰盛的时候。巴掌大的地方,被我收拾得满满当当。黄瓜挂在架上,西红柿涨红了脸,茄子紫莹莹的,生菜、菠菜绿得发亮。随手摘一把香菜,洗洗就能下锅,全是太阳和泥土给的滋味,吃得踏实。
秋天就更不用说了。开荒得的那片地,花生和红薯挖出来时,带着一股子鲜甜的土腥气。玉米秆子高过头顶,掰下的玉米棒子,留着清香的汁。梨园里的果子沉甸甸地压着枝头,咬一口,水汪汪的甜。那时候,猫儿狗儿跟着我在院里转悠,心里被一种饱满的宁静填得满满的。正如自己随口吟的那般:
金秋十月高阳暖,
家山漫岭黄灿灿。
猫前犬后庭园遛,
儿女左右心相连。
美,是真美。
可一到冬天,光景就大不一样了。老宅空旷,只能靠一个煤炉子和一面土炕取暖,跟城里有暖气的楼房没法比。最怕下大雪封了山,早晨起来,屋里冷得像个冰窖。第一件事就是鼓捣那炉子:清理灰渣、找柴火、引火、添煤……一番折腾下来,手是黑的,鼻尖是黑的,常常呛得直咳嗽。可就算这样,屋里也难得超过十度,坐着不动,寒气就从脚底往上钻。
我总觉得自己还不算老,还能应付。直到今年冬天,一场雪后,女儿女婿突然回来了,不是空手,而是带着几位师傅,拉来了一车东西——钢管、暖气片,还有个铮亮的小锅炉。我愣在门口,他们却笑着推我进屋:“爸,今年咱不用受那烟熏火燎的罪了。”
几个师傅手脚麻利,叮叮当当,不到两小时,一套像模像样的水暖系统就接好了。女儿在一旁递工具、说主意,女婿陪着师傅上上下下。我站在那儿“监工”,看着他们年轻人动作流畅、默契配合的样子,忽然间就明白了:不是活儿变得容易了,是我的手脚,到底跟不上从前了。
炉火点起来的那一刻,暖气片慢慢热了,一股温温的暖意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猫儿好奇地凑过去,贴在旁边舒服地蜷成了团。我望着窗外还未融尽的积雪,心里那点冬日的萧瑟,一下子被烘得软软的、暖暖的。
那天晚上,我提笔写了一首小诗:
暖炉新立散温光,
一室融融御冷霜。
儿女心孝驱岁寒,
山居冬月也芬芳。
是啊,冬天还是那个冬天,山也还是那座山。但因为有了这点暖,有了这份心,往后的每一个寒冬,大概都会飘着淡淡的芬芳吧。
(朱志勤,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助理工程师。文学的力量让自己融入自然、融入和谐,永远年轻永远热血沸腾。)
发布于:北京市金御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环球策略 枭龙战斗机为何突然成了香饽饽,意向订单有多少架了?
- 下一篇:没有了